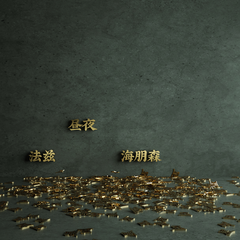死海 Dead sea
歌手:法兹乐队 FAZI
发行时间:2018-01-26
发行公司:
死海,位于以色列和约旦的交界处,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咸水湖,据说人可以直接躺在湖面上,而不会沉下去,这样的景象或多或少会让我想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。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故事,是关于中国的死海。虽然这个地名在任何官方出版的中国地图上都找不到,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不过这个地方一直停
死海,位于以色列和约旦的交界处,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咸水湖,据说人可以直接躺在湖面上,而不会沉下去,这样的景象或多或少会让我想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。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故事,是关于中国的死海。虽然这个地名在任何官方出版的中国地图上都找不到,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。不过这个地方一直停留在王源的记忆里,在她头脑里最深的某个角落,这个名字总是一再地出现,很多年也未曾中断。
大约从10岁开始,王源就随着父亲开始一次一次的搬家。即使在我和她交往的那几年里,她也很少提起那些过去的往事,但是我大概也能猜得到,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学校,南方城市的某个下雨的清晨,大雪封山的北方的冬天,以及火车里看见的一闪而过的丘陵,所有这些记忆混杂在一起,童年和少年的经历被互相穿插,被挑选,在一个少女的头脑里起起伏伏,被放大或者被遗忘。所以当王源第一次向我说起死海这个地方时,我难免会觉得,那不过是由于她记忆交错而带来的幻觉。
不是的,绝对,不是幻觉,王源说。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睛,那种出乎寻常地真诚态度让我几乎相信了她。
王源的父亲,王为军,在43岁那年终于停止了搬家,他被调到地质研究所的宿舍小区,负责保卫工作。那年王源16岁,和我一样大。王为军,王源,还有王源的后妈钟阿姨住在4号楼。大家都说钟阿姨是个有背景的女人,所以王为军才可以得到这个工作。要不然,大家都这么说,要不然以王为军的资历,以及他那种温吞吞的性格,怎么可能做到保卫科长。
王为军爱喝酒,我曾经见过他在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就着半盘剩菜喝光了一瓶白酒。后来我跟王源提起过这事,她只是笑笑,什么也没说。
16岁的王源和我成了高中同学,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女朋友。接着就是争吵,和好,分手,再和好,再争吵,这样的情节越来越频繁,最后变得毫无新意,直到我们彻底分手。之后我听说她去了南方,嫁给了一个广东人。再见到她的时候,是在王为军的葬礼上。
不知道为什么,在葬礼上我总是想和王源说说王为军喝酒的事情,尤其是在他和钟阿姨离婚之后,女儿不在身边的这段日子里,我偶尔听到的一些关于酒精是如何让王为军失控的事情。但是王源似乎完全不想听这些。所以她总是沉默。但是除了喝酒之外,我还能对王源说些什么关于她爸爸的回忆呢?等到王为军去世,我才发觉虽然我和他女儿谈了好几年的恋爱,但是对他却是记忆模糊,大概唯一能记得的就是他某天中午坐在明亮的餐桌前,左手举着酒杯右手拿着筷子,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
来,陪我喝点,他对我说。
分手之后我有几次梦到过王源,梦见她在我耳朵边,用低低地声音向我倾诉,说她有多么不快乐。那些梦就像是黑色墙壁上的一个洞,穿过去仍然是黑暗,看不见尽头,也不知道该怎样回头。
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向王源说起这些梦。
葬礼之后王源请我去她家吃饭,算是答谢我为葬礼帮忙,她这么说。另外,她说,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。
那是个关于死海的故事,我一直记得很清楚,她说。我能看出来她已经喝的有点多了,眼神已经变得朦胧,说话时的手势也明显地多了起来。
那年我12岁,那是我们第四次或者第五次搬家,她说,要从秦岭穿过去,到四川的一个什么地方。那时候的秦岭还没有修什么隧道,所以火车走的很慢,沿着山势上上下下,而且经常走走停停,让别的什么车先过。不过因为是地质局工作的原因,我和爸爸可以有卧铺,所以这样的火车其实也不算是太幸苦。我喜欢睡在上铺,躲在最上面的角落里,别的人看不见你。我记得那天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就醒过来了,火车停着,窗户外面有几盏昏黄昏黄的路灯,应该是在一个什么车站,很小的站台。而且一定是很晚了,周围都是打鼾的声音,还有那种典型的火车才有的味道。然后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唱歌的声音,那声音是突然出现的,而且应该就在车厢里面。声音非常非常地低沉,真的是低沉到我没法形容。是一个老人的声音,唱的什么我听不清,但是那个旋律,那个音调,就像是在祈祷,就像是因为生活的不幸而向某种事物祈祷。那个时候我就呆呆地听着,一动也不敢动,就好像空气中的任何变化都会打断这个唱歌的声音,就是那种敏感和脆弱的感觉。
她停下来,端起酒杯喝了一口,然后举着酒杯盯着里面剩下的小半杯酒,看了好一会儿。然后她说,你知道吗?这瓶酒是我爸特意留着的,说是要等我结婚后和他女婿一起喝。虽然我的婚也结了,却也始终没赶上机会喝,没想到,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,不过,你也算是半个女婿吧。
我没说话,我想在这种时候我最好还是不说话,我在等她接着说她的故事。
那个老人唱歌的声音一直没停,慢慢地我的脑子就空了,感觉就是一片空白,我忘了我在什么地方,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反正就是一片空白,就好像脑子完完全全停止了,自我彻底地消失了。直到车轮动了一下才把我惊醒,真的是被惊醒的。那一瞬间我还是根本想不起来我是在什么地方。但是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,就好像是我的一生已经过完了,现在是一个完完全全新的现实世界,头脑异常地清醒。那个唱歌的声音已经没有了,周围还是一片打鼾的声音,还是同样的火车的味道。然后我看了看窗户外面,路灯慢慢地闪过。在站台的最后我看见这个车站的名字,叫死海。
然后呢?我问。
没有然后了,王源说,她的神态正在变得正常,酒精正在消解,眼神恢复到一如既往的清澈。只不过那天夜里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,她接着说,就是不管你经过多少个车站,换过多少个城市,住过多少个房间,最终能在你心里留下来的,恐怕也不过是那么一段最模糊和最脆弱的声音。
这恐怕是你的幻觉吧,这是我当时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。